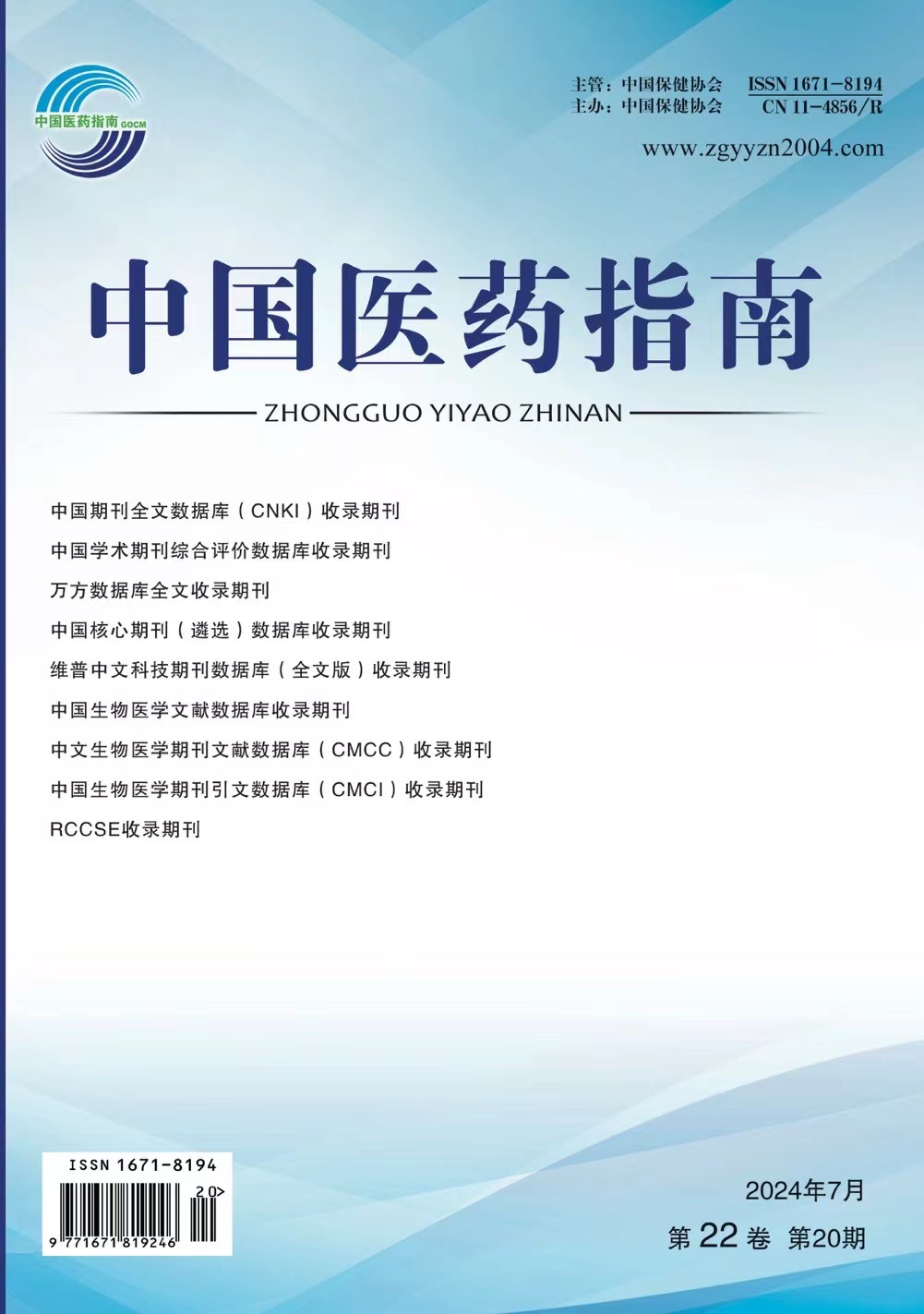伤寒研读
试论《伤寒论》中的若干辩证法思想
金寿山
【摘要】
【关键字】
中图分类号:文献标识码:文章编号:
试论《伤寒论》中的若干辩证法思想
《伤寒论》一书,历代评价很高。注解此书者,自金成无己以下,不下数百家。这些注解,一方面阐发了《伤寒论》,一方面又丰富和发展了《伤寒论》。在热性病方面,发展为温病学说,在内伤杂病方面,亦为后世各家学说的渊源。
仲景在本书中总结了古代人民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,在继承《内经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大步,把疾病的各种证治加以概括,以阴阳为纲,六经为目,确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原则。正如清柯韵伯所说:“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,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。”徐灵胎也说:“医者之学问,全在明伤寒之理,则万病皆通。”这个“理”究竟是什么呢?个人体会,主要就是指其中所包含着的若干辩证法思想,尽管是朴素的、自发的,然而内容是丰富的、具体的,它体现于“六经”辨证、“八法”论治之中而统率着“方”和“药”,构成了中医学特有的一套理、法、方、药完整体系。尽管治病的方、药在后世已大有发展,不为《伤寒论》所局限,但是他所论的理、法却可以普遍应用,在一定历史时期内,起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。
本文结合个人学习自然辩证法的体会,试图从邪与正、标与本、常与变、阴与阳几个范畴初步探讨它的若干辩证法思想。为了说明问题起见,除《伤寒论》原文之外,并引用《内经》以及后世各家学说,作为补充论证。
一、 邪与正
何谓“邪”?一般指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淫之邪以及时气、疫气、厉气等外邪而言。引申言之,凡一切致病因子及其所产生的破坏力,都可称为“邪气”;何谓“正”?“正”系相对于“邪”而言,“正气”为人身的真气,生命活动的基础,凡防御与抵抗疾病与本身康复的功能皆属之。邪与正的关系,是相当复杂的,其中一部分牵涉到哲学上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。
中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原因有两方面: 一方面由于正虚,是内因,是决定性的因素;另一方面由于邪气,是外因,是致病的条件。早在《内经》就有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的看法,《伤寒论》基本上继承了这个看法,其辨证论治首先着眼于正气。如原文第7条说:“病有发热恶寒者,发于阳也;无热恶寒者,发于阴也……”同一伤寒病,发于阳者表现为发热恶寒,发于阴者表现为无热恶寒,这是由于正气有较强、较弱之不同所致。钱潢谓之因发知受。又如太阳病发汗后的变证有身疼痛、脉沉迟(营血素亏)者;有腹胀满(脾阳素弱)者;有心悸、头眩、身动、振振欲擗地(肾阳素虚)者……主要也是由于正气反应不同所致。
《医宗金鉴》说:“六气之邪,感人虽同,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,何也?盖以人之形有厚薄,气有盛衰,脏有寒热,所受之邪,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,故生病各异也。”所以《伤寒论》的辨证,首先是分六经,而辨其伤于寒抑是中于风则是次要的。其立法论治的要旨,一是扶阳气,二是存津液。观其立方,桂枝、四逆、理中、复脉等方在论中占着重要地位;观其用药,桂枝与甘草、芍药与甘草、人参与甘草、干姜与附子常用以相伍,作为扶阳或益阴之用。而对于咽喉干燥者、淋家、疮家、衄家、亡血家、汗家,皆在禁汗之列。因为这些病人,或为阴虚、或为阳虚、或为气血俱虚,皆属正气不足,发汗足以重伤正气,引起变证。可见《伤寒论》是处处重视正气的。
但是,《伤寒论》之重视正气,并不等于对外来的邪气置之不顾;并不意味着治病的方法就是一概扶正补虚。须知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的“虚”,是相对的虚,是从发病学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,并不等于发病后所表现的证候一定是“虚证”。恰恰相反,既病之后,成为邪正相搏的局面,在很多情况下,是表现为“实证”的,《伤寒论》就以祛邪为主。这种情况,前人有称之为“虚处受邪,其病则实”。所谓“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”的说法,必须与这两句话连起来看,方才全面。
尽管医生立方遣药的主导思想是扶助正气战胜邪气,使其“正胜邪却”,但手段却是多种多样的,而祛邪正是相对于扶正的一大法,只要去邪而不伤正,那么邪去则正自安。在表寒里热之证,可以投大青龙汤发汗而不嫌其峻,因为大青龙汤证见无汗、高热、烦躁,汗不出则热不除,热不除津液将更伤,权衡其利害轻重,虽服药后可能大汗,损伤一些津液,但只要病解津液自能恢复;在阳明大热大实之证,《伤寒论》认为,发展下去就会热盛伤阴,土燥水竭,导致死亡,须及时用大承气汤急下邪热以存阴津。这些例子说明,《伤寒论》认为在一定条件下,当邪气对于疾病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时,就应以祛邪为主。
《伤寒论》八法中的汗、吐、下、清等法,基本上都是祛邪之法;《伤寒论》所用的药物,如麻黄、瓜蒂、芒硝、大黄、石膏、知母、黄芩、黄连等,都是祛邪之药。这些祛邪的方法和药物不但用于三阳病,在一定的条件下,即便是三阴病,也仍然有应用的机会。例如“厥阴病”篇:“伤寒六七日,大下后,寸脉沉而迟、手足厥逆、下部脉不至、咽喉不利、唾脓血、泄利不止者为难治,麻黄升麻汤主之。”方后云:“汗出愈。”厥阴病寒热错杂,存在着阴尽阳复之机,在一定条件之下,如本证上热闭塞,兼虚其中,可以合发表、清上、温中于一方治之。在临症时确有此种方证,如张路玉医案:
“陆中行室,年二十余。腊月中旬患咳嗽,挨过半月,病热稍减。新正五月,复咳倍前、自汗体倦、咽喉干痛。至元夕,忽微恶寒发热,明日转为腹痛自利、手足逆冷、咽痛异常。又三日则咳唾脓血。张诊其脉,轻取微数,寻之则仍不数,寸口似动而软,尺部略重则无。审其脉证,寒热难分,颇似仲景厥阴例中麻黄升麻汤证。盖始本冬温,所伤原不为重,故咳,至半月渐减,乃勉力支持岁事,过于劳役,伤其脾肺之气,故咳复甚于前。至望夜忽憎寒发热,来日遂自利厥逆者,当是病中体疏,复感寒邪之故。热邪既伤于内,寒邪复加于外,寒闭热邪不得外散,势必内奔而为自利,致邪传少阴厥阴,而为咽喉不利唾脓血也。虽伤寒大下后与伤热后自利不同,而寒热错杂则一。遂与麻黄升麻汤一剂,肢体微汗,手足温暖,自利即止。明日诊之,脉亦自和。嗣后与异功、生脉合服,数剂而安。”
又如少阴病,始得之,反发热脉沉者,用麻黄附子细辛汤。按少阴病禁发汗,今麻黄、细辛合用,其发汗力量自较单用麻黄者为强,用于少阴病似属不可理解。不知本病初起即现少阴证,固属正气衰弱,但发热无汗,其势又须从表解,所以本方既用麻黄、细辛以祛邪发汗,又用附子扶阳助正,防其大汗之虚脱。用峻药目的正是为了患者正气之虚弱,必须一战而成功。假如不认识这一点,只知扶正而不敢祛邪,或祛邪而用药不够,就很难收到满意的效果。如吴鞠通治一水肿病人,前医曾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无效,吴仍用之而奏效。关键在于前医恐麻黄发阳,仅用八分,附子用一钱以监麻黄,又恐麻黄、附子药性皆慓悍,用一钱二分甘草以监制麻黄、附子。吴则反是,重用麻黄,附子用量则少于麻黄,甘草用量又少于附子,使麻黄、附子充分发挥作用。这些例子可以说明,以祛邪为主的方法,只要与具体病情合拍,即使在三阴病证,也是可以恰如其分地来使用的。
综上所述,《伤寒论》对于邪正关系的看法,认为正虚是发病的根据,邪凑是发病的条件,而疾病发展的过程则是邪正相搏的结果。治病既要重视正气,又不能无视邪气。《伤寒论》中许多治法与处方,既是扶正,又是祛邪,扶正与祛邪,很难截然分开。如桂枝汤既为调和营卫(扶正)之主方,亦为解肌疏风(祛邪)之要药;小柴胡汤既有柴胡、黄芩之清热,复有人参、甘草之益气,合用于一方起着扶正达邪之作用。但须指出,所谓祛邪与扶正不能截然分开,不是说不要有重点,大致祛邪的方法以发表攻里为先;扶正的方法以滋阴扶阳为主。邪气盛,正气未衰 时,以祛邪为主,邪去正乃安;正气虚,虽见邪盛,一般以扶正为主,正足邪自去。但也须看具体病情,具体分析,不能执一而无权。总的目的,是为了去病,为了解决邪、正之间的矛盾。病去则体虽虚,多有生存之希望;病留则体虽壮实,亦有死亡之可能。用之得当,大黄、芒硝就是存阴之药,有利于正气;用之不当,人参、甘草恰恰为留邪之药,无益于正气。
《伤寒论》第58条说:“凡病,若发汗、若吐、若下、若亡血、亡津液,阴阳自和者,必自愈。”因此,在正确辨证的情况下,并在一定限度以内使用汗、吐、下的方法,在表面上虽似丧失了津液,损伤了正气,实际上是不逆病机,达到了祛邪的目的,解决了正邪相搏的矛盾,恰恰没有损害正气。《伤寒论》就是这样辩证地看问题的。
二、 标与本
《伤寒论》辨证论治的基本精神是“治病必求于本”。“本”是什么?《内经》说:“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,万物之纲纪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,神明之府也,故治病必求于本。”所谓“本”,指的就是阴阳。《内经》又说:“善诊者,察色按脉,先别阴阳。”说明掌握疾病内在的矛盾——阴阳,是辨证的首要任务。从辨证的角度上来看,所谓阴阳,就是病位之表里、病状之寒热、病情之虚实,这是《伤寒论》全部立法的依据。
相对于本者为标。病因为本,病状为标;内在为本,外表为标;标发现于表,本多隐伏于里。总之,标本的关系,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。标本一致,表现为真寒、真热的病状者易辨;标本不一致,表现为假寒、假热的病状者难识。《伤寒论》第11条说:“病人身大热,反欲得衣者,热在皮肤,寒在骨髓也;身大寒,反不欲近衣者,寒在皮肤,热在骨髓也。”程应旄释之曰:“病人身大热,反欲得近衣者,沉阴内锢而阳外浮,此曰表热里寒;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,阳邪内菀而阴外凝,此曰表寒里热。寒热之在皮肤者,属标属假;寒热之在骨髓者,属本属真。本真不可得而见,而标假易感,故直从欲不欲断之,情则无假也。不言表里,言皮肤、骨髓者,极其浅深,分言之也。”这是说,在标本不一致的情况下,必须把本质探求清楚,勿为假象所迷惑。在后世医家,对于辨别标本的真假,是极为注意的,如:
(1) 王海藏治侯辅之病,脉极沉细,内寒外热,肩背胸胁斑出十数点,语言狂乱。肌表虽热,以手按执须臾冷透如冰。断为外假热而内真寒,与姜、附等药二十余两,乃大汗而愈。
(2) 李士材治一人,精神困倦、腰膝异痛不可忍,众医皆以为肾主腰膝而用桂、附。绵延两月,病者愈觉四肢痿软、腰膝寒冷,愈以为寒,恣服热药。李诊之,脉伏于下,极重按之,振指有力。因思阳证似阴,乃火热过极,反兼胜己之化,小便当赤,必畏沸汤,询之果然。乃以黄柏三钱,龙胆草二钱,芩、连、栀子各一钱五分,加生姜七片为向导,乘热顿饮,移时便觉腰间畅快。三剂而痛若失。
上引二案,在辨证方法上,如辨脉、辨热、辨小便、辨渴、注重病人的体征等,较之《伤寒论》更为细致深入,但其思想,还是在《伤寒论》的指导之下。
标与本的关系,既然是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,它必然有内在联系。尽管有时二者不相一致,出现假象,但是任何现象脱离不了本质,这一个假象,仍然是从本质上产生。《伤寒论》对于这些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之证的处理,就是认识到标出于本,标一定与本有联系,因而认识疾病的性质更为深入。举真寒假热证为例:“少阴病,下利脉微者,与白通汤;利不止,厥逆无脉,干呕烦者,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。服汤脉暴出者死,微续者生。”(《伤寒论》第315条)本条以葱白、干姜、附子治其下利不止,厥逆无脉之真寒;以人尿、猪胆汁治其干呕而烦之假热,即一般认为寒凉反佐热药之法。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不用黄芩、黄连等大苦大寒之药而用人尿、猪胆汁咸苦相伍来作反佐呢?根据阴阳理论来分析,本证假热之所以出现,一方面由于阴邪内盛,真阳为阴邪所逼而上浮;另一方面又由于阴邪内盛,以致或吐、或利、或吐利交作,亡失津液,真阴亦已不足,阴不恋阳,形成“脱”证。其所以用人尿、猪胆汁,不仅仅寓有反佐的意义, 更重要的,是含有咸苦滋润、从阴引阳之作用在内。假如用芩、连等大苦大寒之药来作反佐,不但没有这个作用,甚至可能化燥伤阴,其结果,阳不能回或阳回而阴竭亦死。可以看出,《伤寒论》对于本证的处理,系以“阴阳消长”“阴阳互根”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作指导,一面破阴(邪)回阳(正),一面从阴(正)引阳(正)。
上引条文中“服汤脉暴出者死,微续者生”二语,亦同样说明了现象与本质的真假之间的辩证关系。因为这种危笃之证,厥逆无脉,不可能突然转好,服白通加猪胆汁汤后,脉暴出是虚假的,是脉气一时为药力所迫,药力尽则正气仍绝故死;脉微续是正气逐渐恢复,才是真正好转故生。这是仲景在实践观察中如实反映的客观实际。
标本关系表现于寒热方面的情况已如上述,表现于虚实方面也是如此。在一般的虚证与实证,比较容易辨别。但在病笃的情况下,所谓“至虚有盛候,大实有羸状”往往出现假象。如《伤寒论》阳明病中提出脉迟、短气、循衣摸床、惕而不安等证,就是注意到“大实有羸状”;少阴病中提出脉紧、烦躁、谵语、口渴、面赤等证,就是注意到“至虚有盛候”。假如细心观察,假象是可以辨识的。如:
李士材治韩茂远病伤寒。九日以来,口不能言、目不能视、体不能动、四肢俱冷,皆曰阴证。士材诊之,六脉皆沉;以手按病人之腹,病人两手护之,眉皱作楚;按其趺阳,大而有力。乃知其有燥屎,以大承气汤下之,得燥屎六七枚,口能言,体能动矣。
以上所引,就是从羸状之中辨识其有大实的医案之一。所以古人有这样一个经验: 见到通体皆现虚象,一二处独见实证,此实证必须重视;见到通体皆现实象,一二处独见虚证,此虚证也必须重视。张景岳称之为“独处藏奸”。医生遇到这种情况,必须探求其本质。假如“省疾问病,务在口给,相对斯须,便处汤药,按寸不及尺,握手不及足,人迎趺阳,三部不参,动数发息,不满五十,短期未知决诊,九候曾无髣髴,明堂阙庭,尽不见察”是张仲景所最反对的,认为“夫欲视死别生,实为难矣”。
《伤寒论》反复辨明病起何因;前见何证,后变何证;恶寒恶热,寒热轻重,昼夜轻重;有汗无汗,汗多汗少,汗起何处,汗止何处;口淡口苦;渴与不渴,思饮不思饮,饮多饮少,喜热喜凉;思食不思食,能食不能食,食多食少;胸、心、胁、腹有无胀痛;二便通涩,大便为燥为溏,小便为清为浊,色黄色淡;曾服何药,药后变化如何……脉症合参,或拾症从脉,或拾症从证,经过思考分析,才能深入了解到疾病的本质,作出正确的判断。如《伤寒论·阳明病》篇有两条条文,其一是:“阳明病,自汗出,若发汗,小便自利者,此为津液内竭,虽鞕(指大便硬——笔者注)不可攻之,当须自欲大便,宜蜜煎导而通之。”另一条是:“病人小便不利,大便乍难乍易,时有微热,喘冒不能卧者,有燥屎也,宜大承气汤。”从表面看来,前者大便硬,应予攻下;后者大便乍难乍易,不宜攻下。但经过分析,知前者为津液内竭(临床上多见于阳明病之恢复期),而非热结于里,大便虽硬却不可攻;后者为燥屎内结,有喘冒不能卧之证,大便乍难乍易乃是“热结旁流”,却宜大承气汤。施治的熨贴,就在于辨证的精细,其原则就是“治病必求于本”。
三、 常与变
常与变的关系,这里指的是一般性与特殊性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。
《伤寒论》的理论是在《素问经·热论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《素问·热论》只论述热病的一般性;《伤寒论》则是从认识热病的一般性发展到认识热病的特殊性,进而把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,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。例如《素问·热论》对于热病分六经形证;《伤寒论》也分六经形证,但其三阳病与前者不尽相同,而在三阴病且有相异之处。这是因为,前者只论热病之常而不及其变,六经传受皆是热证,后者则是备论热病之常与变,认为六经病有热证也有寒证,有实证也有虚证,此其一;
前者只从人身经脉循行部位说明六经的病理而不及六经之标本、气化,后者除了以经络学说为根据之外,还运用了脏象、标本、气化等理论。如论太阳病除可见到头项痛、腰脊强外,更主要的是发热、恶寒、脉浮,阳明病除可见到身热、目疼、鼻干、不得卧外,更主要的是胃家实证,少阳病除可见到胸胁痛、耳聋外,更主要的是寒热往来、口苦、咽干、目眩、心烦、喜呕,太阴病除可见到腹满、嗌干外,更主要的是吐利、食不下,少阴病除可见到口燥、舌干而渴外,更主要的是脉微细、但欲寐,厥阴病除可见到烦满、囊缩外,更主要的是厥热交替,寒热错杂等证,此其二;
前者论传经,日传一经,由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,循次传受,后者则不为日数所限制,可以循经传,也可以越经传,而且可以不传,传与不传以及传入何经,惟以客观表现的脉证为依据,此其三。
至于治法方面,前者只是原则性地提出汗、泄二法;后者发展为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八法。总之,后者是仲景通过平脉辨证,反复实践,从中认识到许多脉证的特殊性和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发展规律,因而对于疾病的本质,认识得更为全面,更为明确。
《伤寒论》的六经提纲,言简意赅,概括性很强。例如: 太阳病以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,脉浮是定其病位之在表,头项强痛、恶寒是定其主证;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,一系列的大热大实证都被包括在内;少阴病以脉微细、但欲寐为提纲,由于少阴病属心肾病,脉微细、但欲寐,已经抓住心肾不足之主要关键;少阳病为阳枢,变化很多,《伤寒论》于少阳病,举提纲与小柴胡汤主证之外,特别提出凡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,不必悉具,指出了少阳病的特性……总之,《伤寒论》辨六经之病,离不开具体内容的概括,此即六经病之常;但每一个具体脉证,又都不是完全地包括在提纲之中,此即六经病之变。六经病的常与变,就是这样辩证地互相联结着的。
常与变的对立统一关系,还体现在《伤寒论》的立法处方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方面。举太阳中风证为例: 头痛发热、汗出恶风、脉浮缓,是中风正证,用桂枝汤是常法;加葛根,加厚朴、杏仁,加苓、术……随证加减,都是变法。但是,这些均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减,基本上还是太阳中风证。但在太阳篇第20条:“太阳病发汗,遂漏不止,其人恶风、小便难、四肢微急难以屈伸”,用桂枝加附子汤,这就不是随证加一味药的问题,而是变调和营卫之剂为扶阳救逆之方。本条为汗后变证,其人恶风为太阳中风之表邪仍在;汗漏不止为卫阳虚弱;小便难、四肢微急、难以屈伸为津液不足。按照阴阳的理论来分析,人以阳气为本,“阳者,卫外而为固也”,“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”,患者阳气之强弱,特别是对于伤寒一类疾病(寒为阴邪,伤人之阳)的预后,是起着决定的作用的。本证由于卫阳不固而致汗漏不止,而汗漏不止,阳从汗出,更促使卫阳虚弱,足以导致亡阳虚脱之危险,这是必须加以纠正的。至于太阳中风之表邪,虽然仍然存在,而小便难、四肢微急,难以屈伸,属阳不生阴而致津液不足,则均属于次要地位。仲景抓住了卫阳虚弱这个主要环节(主证),于桂枝汤原方中加一味附子,桂附相合以温煦阳气,卫阳复振,邪自去,表自解,阴自复,津自生,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。反之,如《伤寒论·太阳篇》第29条所说:“伤寒脉浮、自汗出、小便数、心烦、微恶寒、脚挛急,反与桂枝汤欲攻其表,此误也。”所以误治,就是由于分不清主次,认识不到各个矛盾之间的互相联系。
由此可见,《伤寒论》由于认识到各个病证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,能够从中分清主次,提出了可汗、不可汗;可下、急下、不可下;可吐、不可吐;可温、急温等等具体而灵活的不同治疗法则,是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的。如: 太阳病可发汗是常法,不可发汗是变法;阳明病可下是常法,不可下是变法;少阴病可温是常法,可清是变法;表里兼见之证,先表后里是常法,先里后表是变法。病有发热恶寒之表证,复有心下痞之里证,当先解其表,后攻其痞;病有协热下利、利下不止、心下痞硬者,表证未除,里虚又见,治宜表里兼顾而侧重于温里;病有下利清谷不止、身疼痛者,同样既有表证,又有里证,但下利而至清谷,里证已急,必须急救其里,后解其表。总之,寒者温之、热者寒之、虚者补之、盛者泻之,这是《伤寒论》治病的原则性;“观其脉证,知犯何逆,随证治之”,这是《伤寒论》治病的灵活性;原则性与灵活性之能很好结合,则在于“审察病机,无失气宜”。
四、 阴与阳
中医学范围内的阴阳学说,其理论具备于《内经》。《内经》认为阴阳是“道”,有胜复,有消长,互相依存,互相转化。任何具体事物都有或阴或阳的属性,并且认为事物之间彼此都有联系,阴中有阳,阳中有阴,阴阳就是万物的根本。兹就《伤寒论》的辨证论治、立法处方中间所体现着的这个精神加以探讨。
在疾病过程中,外邪及其所产生的破坏力,不属于阴,即属于阳,故有阴邪、阳邪之称。阴则为寒,阳则为热,与之相对的一方则为正。例如: 寒邪(阴邪)伤阳之阳,即正气一方面的阳气;热邪(阳邪)伤阴之阴,即正气一方面的阴气(或称阴津、阴液)。在生理状态下,阴阳是调和的(相对的平衡);在病理状态,阴阳是失调的。正能胜邪,疾病趋向好转,最后正胜邪却,阴阳自和(恢复生理上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)而告痊愈;正不胜邪,疾病就趋严重,甚至导致阴阳离决而告死亡。其表现于外的脉证,也即是邪气的破坏力与正气的抗病力的综合反映。《伤寒论》把它分为三种阳证与三种阴证。以三阳病证而言,阳道实,实者邪气盛也,但正气有能力足以敌邪,故表现为阳证(亢奋的、实热的证候),施治的重点是在祛邪,或汗、或清、或下、或和解,因势利导,随证制宜,使其正胜邪却;三阴病证者,阴道虚,虚者精气夺也,为正气衰弱抗病力不强所致,故表现为阴证(衰弱的、虚寒的证候),虽反应不甚强烈,必须引起重视。例如《伤寒论》第61条:“下之后,复发汗,昼日烦躁不得眠,夜而安静,不呕不渴,无表证,脉沉微,身无大热者,干姜附子汤主之。”本证白昼虽见烦躁,但夜而安静,不呕不渴,身无大热,证似非重,势似非急,然而《伤寒论》却用干姜附子汤顿服,因为这是阳微阴躁,四逆之渐,不可轻视。所以《伤寒论》对于三阴病施治的原则是扶正而不是祛邪。如“少阴病”篇提出:“少阴病,脉沉者,急温之,宜四逆汤。”“少阴病,脉微,不可发汗,亡阳故也;尺脉弱涩者,复不可下之。”因为,汗、下是亡津液、伤阳气的,用于正气不足者,可能邪未去而正转伤,也可能邪虽去而正亦随之而脱。
如上所述,疾病的转归,取决于邪正势力之消长。三阴病证虽属阴盛阳衰,亦即邪盛正衰,但只要阳气不绝,到一定阶段,具备了一定条件,便会向阴消阳长转化,古人朴素地认作为物极必反,有胜必有复。例如《伤寒论》的厥阴病是六经中的最后一经,为阴之尽(极点),按理说,厥阴病应重于少阴病,但《伤寒论》举死证者,少阴特多而厥阴反少,正因为一线之生机,即在此阴尽阳生之时。丹波元坚说:“厥阴则寒热相错,用药有所顾忌,然比之少阴之纯寒,犹有阳存耳。”仲景“厥阴病”篇以厥少热多断为其病当愈;以厥多热少断为其病为进。所谓“厥”,是指四肢厥逆,是阴胜的表现,厥之多少,标志邪气之进退;所谓“热”,是指发热,是阳复的转机,热之多少,标志正气之消长。阳气长,其病当愈;阳气退,其病为进。仲景不独在“厥阴”篇中已明确指出,在“少阴”篇决死生的几条中,以手足温、时自烦为阳复佳兆,可治;厥逆不回、脉绝不止、躁扰不安为阳绝恶候,主死,也同样体现着这一精神。所以,治疗阴证,法当急温,使其阴证转阳,然后“随证治之”。但如仲景“厥阴”篇的喉痹、便脓血等证,皆属阳复太过之证,则又必须适当调整,始为合辙,倘失其机,亦为偏害。
有胜必有复是古人认识阴阳转化的规律。阴证固能转阳,而阳证亦能转阴。例如阳明病大热、大渴、大汗出、脉洪大,是典型的阳、实、热证。当其阳盛之时,一方面是邪气盛,一方面是正气反应强烈,但反应过于强烈,就是“亢阳”,又会给正气本身带来一定的损害。故在太阳病之阳证,可以发表不远热,而在阳明病之阳证,则于法当清,若任其亢阳无制,既能亡阴(正阴),亦能亡阳(正阳)。徐灵胎曾经指出:“亡阴不止,阳从汗出元气散脱,即为亡阳。”从亡阴而至亡阳,在证候上的表现来看,是从阳证转为阴证;从病邪一方面来看,已从阳邪(热邪)转化为阴邪(寒邪);从正气一方面来看,阴阳是互根的,阴亡阳亦随之而脱。在治法上这时应以扶正为主,正足邪自去,而扶正则应阴阳(正阴正阳)兼顾。
《伤寒论》于白虎加人参汤证指出“热结在里,表里俱热”,同时又举出有“时时恶风”“背微恶寒”等证,这些证候,就是阳气由盛趋衰之先兆。白虎汤所以加人参,既为承制亢阳,资生化源,且防止热极津亡,阳从汗出,元气散脱,导致亡阳之危险。吴鞠通《温病条辨·上焦篇》第八条说:“太阴温病,脉浮大而芤,汗大出,甚至鼻孔扇者,白虎加人参汤主之;脉若散大者,急用之,倍人参。”自注曰:“浮大而芤,几于散矣,阴虚而阳不固也,补阴药有鞭长莫及之虑,惟白虎退邪阳,人参固正阳,使阳能化阴,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。汗涌、鼻扇、脉散,皆化源欲绝之征兆也。”这是《伤寒论》白虎加人参汤证的一个良好注释。
由此可见,阴与阳的关系,是非常错综复杂的。因一定的条件,一面互相对立,一面又互相联系,互相渗透,互相依存。所谓“阴阳”消长,在病理过程中,亦即“邪正”互为消长。阴盛而阳衰,必迅至有阴而无阳;阳盛而阴衰,必渐成亢阳而亡阴。但同时又有胜复,阴胜则阳复,阳胜则阴复,正因为如此,故阴证有回阳之机转,热病有复阴之可能,而扶阳抑阴或济阴和阳之施治在于及时,方能不失病机。所谓“阴阳”互根,是指正阴(阴液)正阳(阳气)而言,阴亡阳不能孤立,阳亡阴不能独存,相维则生,相离则死。在病理上往往见到高热亡阴,阳亦随之而脱,故治其热必兼顾其阳;吐利伤阳,阴亦随之而竭,故治其寒必兼顾其阴。行救阴救阳之法,必须明阴阳互根之义。
还必须指出,所谓阴阳胜复,绝不是循环现象的重复,而是运动发展的。近人恽铁樵说:“热病虽千变万化,不外《内经》阴胜则寒,阳胜则热;阳虚则寒,阴虚则热数语。此四语,一步深一步。第一步之阴胜则寒(指太阳病未发热之恶寒——笔者注),即伏第二步之阳胜则热;第二步之阳胜则热,正从第一步之阴胜则寒来,故曰阴胜则阳复,盖胜则必复,乃体工之良能;其少阴病之阴争于内,阳扰于外,至于亡阳者,乃第三步,盖体温之集表者失败于外,斯病邪之入里者猖獗于内,是为阳虚则寒;而第四步之阴虚则热,亦正从第三步之阳虚则寒来,何以然?有第三步之寒,斯有第四步之热,乃经文重寒则热之理也。”《伤寒论》论述病证的精神,确是如此。从阳证转阴之恶寒,与太阳病之恶寒,症象虽相似,但前者属虚,后者属实,前者宜温,后者宜汗,本质大不相同;从阴证复阳之发热,与太阳病之表热、阳明病之里热,本质也大有分别,适宜用麻黄、桂枝、白虎、承气汤者毕竟少见,适宜用黄连阿胶汤、复脉汤等方者却较多。恽氏之言,基本上是符合于《伤寒论》的本旨的。
五、 结语
如上所述,《伤寒论》对于疾病证治的认识,是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。正如恩格斯所说:“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之前,就已经按照辩证法来作论断了。”正是这些辩证法思想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,这是极可宝贵的。但同时必须指出,《伤寒论》对于这几种辩证关系,是在朴素的、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之下来认识的,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,不可能辨识很全面,这是受着时代的限制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认识是不可能更进一步深入的。对于这一份宝贵的医学遗产,必须在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之下,来学习继承,整理提高。
金寿山论外感病——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