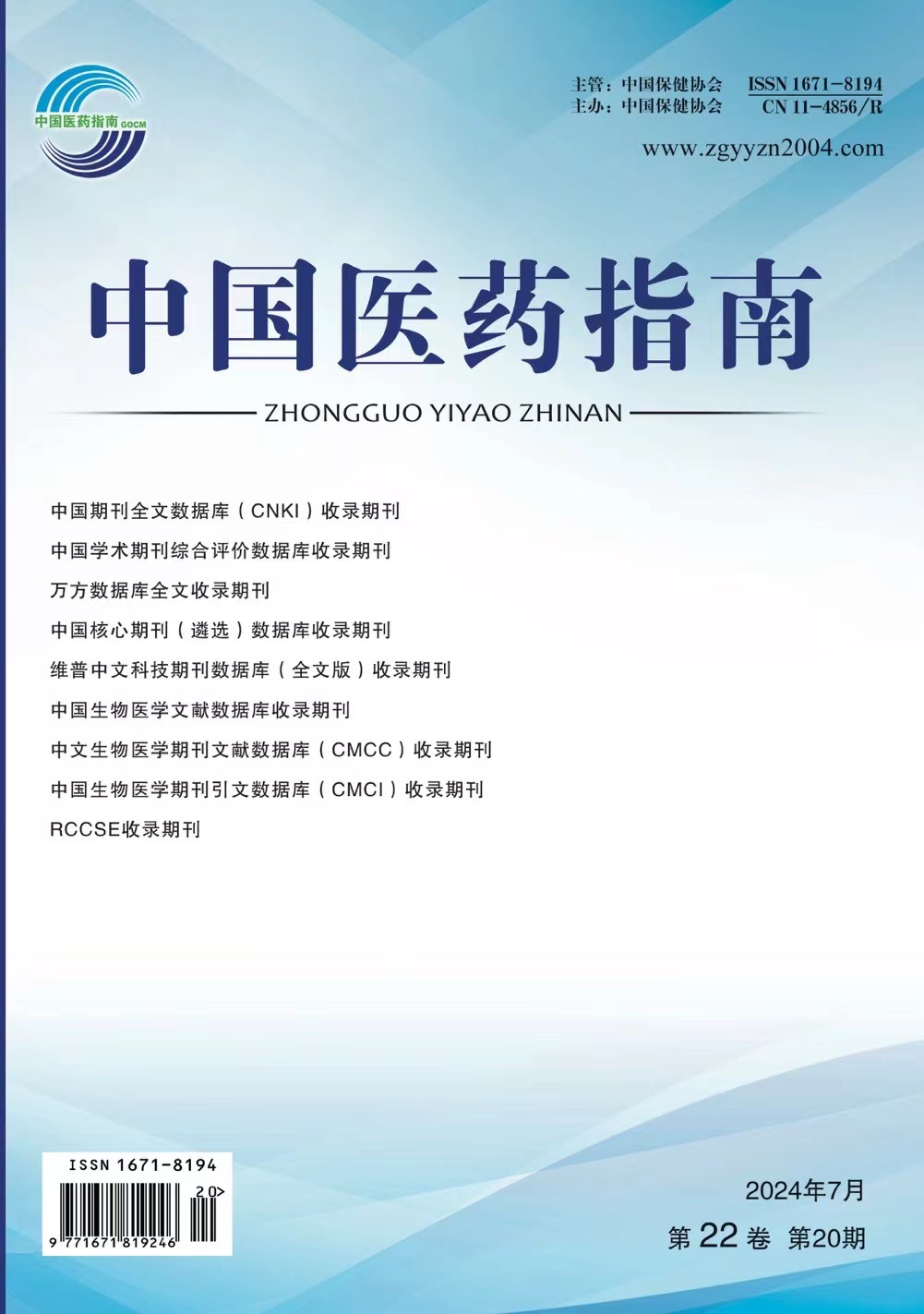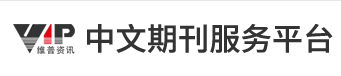内经研读
《本草纲目》的精华在“发明”
丁光迪
【摘要】
【关键字】
中图分类号:文献标识码:文章编号:
《本草纲目》的精华在“发明”
《本草纲目》是中医药文献中的伟大著作,驰誉世界。其中“发明”一项,真是大有发明,为本书的精华部分,突出于同类诸书之上。王世贞称许本书“如入金谷之园,种色夺目;如登龙君之宫,宝藏悉陈;如对冰壶玉鉴,毛发可指数也”。(《本草纲目序》)这在“发明”中都能反映出来。“发明”短小精炼,重点突出,立论精辟,字字珠玑。推为“博而不繁,详而有要,综核究竟,直窥渊海”(王世贞语),洵非虚誉。兹就王氏所云的广、富、透三方面试作介绍,略表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李时珍的敬意。
一、 内容广博
“发明”涉及面很广,真是不仅医书,“实性理之精微,格物之通典”。(王世贞语)如论腊雪,引《释名》:“雪,洗也。洗除瘴疠虫蝗也。”又云:“腊雪密封阴处,数十年亦不坏。用水浸五谷种,则耐旱不生虫;洒几席间,则蝇自去;淹藏一切果食,不蛀蠹。岂非除虫蝗之验乎!”“宜煎伤寒火暍之药,抹痱亦良。”这些知识,是农业生产上总结出来的经验,亦是医学上的妙药。又如对于冰,赞同诸家本草解烦渴、消暑毒之说,更指出“伤寒阳毒,热盛昏迷者,以冰一块,置于膻中良”。开物理降温之先河,良可钦敬。
又如泉水,认为“井泉,地脉也,人之经血象之。须取其土厚水深,源远而质洁者,食用可也。《易》曰: ‘井泥不食,井冽寒泉食’是矣。人乃地产,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,而美恶寿夭,亦相关涉。金石草木,尚随水土之性,而况万物之灵者乎……人赖水土以养生,可不慎所择乎?”这在今天来讲,似已成为人们的常识,但在处理上却并不能令人满意。同时指出,水质不同,作用亦不同,“观浊水、流水之鱼,与清水、止水之鱼,性色迥别。淬剑染帛,色各不同;煮粥烹茶,味亦有异。则其入药,岂可无辨乎”?
又如同一药,由于地区和体质不同,以及古今之异,其用亦殊。如谓:“乌、附毒药,非危病不用,而补药中少加引导,其功甚捷。有人才服钱匕,即发燥不堪;而昔人补剂,用为常药,岂古今运气不同耶?”并指出荆府都昌王、蕲州卫张百户等,日啖附子、硫黄、干姜等,均享高寿;他人服之即为害。“若此数人,皆其脏腑禀赋之偏,服之有益无害,不可以常理概论也。”又《琐碎录》言:“滑台风土极寒,民啖附子如啖芋栗。此则地气使然耳。”
又如忍冬,“昔人称其治风除胀、解痢逐尸为要药,而后世不复知用;后世称其消肿散毒,治疮为要药,而昔人并未言及。乃知古今之理,万变不同,未可一辙论也。按陈自明《外科精要》云: 忍冬酒,治痈疽发背,初发便当服此,其效甚奇,胜于红内消”。洪迈、沈括、僧鉴清等书中所载的疗痈疽发背经验方,皆是此物。
秦汉晋唐,服用丹铅金石之风盛行,流毒甚广,直至明代,但人们犹不知其利弊所在。李氏作了广泛研究,指出其危害。如谓“金乃西方之行,性能制木,故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,而古方罕用,惟服食家言之……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士传流而来,岂知血肉之躯,永谷为赖,可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?求生而丧生,可谓愚也矣”。
至于丹砂,服食的记载更多,而害亦更大,但李氏认为阴极之证,亦有得此而治者。对于石药亦是如此,如谓石钟乳“乃阳明经气分药也,其气慓疾,令阳气暴充,饮食倍进,而形体壮盛。味者得此自庆,益肆淫泆,精气暗损,石气独存,孤阳愈炽。久之营卫不从,发为淋渴,变为痈疽,是果乳石之过耶?抑人之自取耶?凡人阳明气衰,用此合诸药以救其衰,疾平则止,夫何不可?五谷五肉久嗜不已,犹有偏绝之弊,况石药乎”?
李氏还吸收佛道之说,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。如引《楞严经》云:“白旃檀涂身,能除一切热恼。”《杜宝大业录》云:“隋有寿禅师妙医术,作五香饮济人: 沉香饮、檀香饮、丁香饮、泽兰饮、甘松饮,皆以香为主,更加别药,有味而止渴,兼补益人也。”但对《真诰》学道山中宜养白鸡、白犬可以辟邪之说,则斥之为“异端一说耳,鸡亦何神何妖哉!”如此等等,可见其研究发明,涉及面很广。
二、 经验宏富
“发明”集中了历代名家和民间的用药经验,尤其是李氏毕生实践的经验,真可谓价值连城,非常宝贵。如谓芎,“血中气药也。肝苦急,以辛补之,故血虚者宜之。辛以散之,故气郁者宜之。《左传》言麦曲、鞠穷御湿,治河鱼腹疾。予治湿泻,每加二味,其应如响也。血痢已通而痛不止者,乃阴亏气郁,药中加芎为佐,气行血调,其痛立止。此皆医学妙旨,圆机之士,始可语之”。上述二法,笔者应用于临床,可以说屡试屡效,但脾阴虚者不宜用。
又如“骨碎补,足少阴药也,故能入骨,治牙及久泄痢。昔有魏刺史子久泄,诸医不效,垂殆。予用此药末入猪肾中煨熟与食,顿住。盖肾主大小便,久泄属肾虚,不可专从脾胃也。《雷公炮炙论》用此方治耳鸣,耳亦肾之窍也”。在此启发之下,笔者移治肾不纳气的虚喘,形寒汗多,便溏腰痠者,同样获得良效。
牵牛之功,前人褒贬各异。李氏认为:“牵牛治水气在脾,喘满肿胀,下焦郁遏,腰背胀肿,及大肠风秘气秘,卓有殊功。但病在血分,及脾胃虚弱而痞满者,则不可取快一时及常服,暗伤元气也。”并有切身的体验,尝治一宗室夫人,年几六十,平生苦肠结病,旬日一行,甚于生产。但不能服养血润燥药,服之即腻膈;服消黄通利药,亦若罔知。其人体肥而多忧郁,日吐酸痰碗许乃宽。这是三焦之气壅滞,有升无降,津液皆化为痰饮,不能下滋肠腑,非血燥比也。乃用牵牛末,皂角膏丸与服,即便通利。自是但觉肠结,一服就顺,亦不妨食,且复精爽。盖牵牛能走气分,通三焦,气顺则痰逐饮消,上下通快矣。又治外甥柳乔,素多酒色,病下极胀痛,二便不通,不能坐卧,立哭呻吟者七昼夜。病属湿热之邪在精道,壅胀隧路,在二阴之间。乃用楝实、茴香、穿山甲诸药,入牵牛加倍,水煎服。一服而减,三服而平。李氏指出“牵牛能达右肾命门,走精隧,人所不知,惟东垣李明之知之,故明之治下焦阳虚天真丹,用牵牛以盐水炒黑,入佐沈香、杜仲、破故纸、官桂诸药,深得补泻兼施之妙”。阐发深切著明,无以复加。
又如胡椒,不仅临床在用,人们亦喜日常佐餐,而不注意它的利弊。李氏深有体验,指出“胡椒大辛热,纯阳之物,肠胃寒湿者宜之。热病人食之,动火伤气,阴受其害。时珍自少嗜之,岁岁病目,而不疑及也。后渐知其弊,遂痛绝之,目病亦止。才食一二粒,即便昏涩,此乃昔人所未试者。盖辛走气,热助火,此物气味俱厚故也。病咽喉啮者,亦宜忌之。近医每以绿豆同用,治病有效。盖豆寒椒热,阴阳配合得宜,且以豆制椒毒也”。
吴茱萸一物,性味辛温,能散能温,所治之症,皆取其散寒温中、燥湿解郁之功。引朱氏《集验方》云: 常子正苦痰饮,每食饱或阴晴节变率同,十日一发,头疼背寒,呕吐酸汁,即数日伏枕不食,服药罔效。后得吴仙散方服之,遂不再作。每遇饮食过多腹满,服五七十丸便已。少顷小便作茱萸气,酒饮皆随小水而去。前后服痰饮药甚众,无及此者(药用吴萸、茯苓等分为末,炼蜜为丸)。此方确实效佳,笔者曾移治一痰饮眩晕,不能乘车登舟,多年不敢出门,动辄头眩头痛,呕吐清涎酸水之患者,效出意外,病竟就愈,后经多例,同样见效。
李氏对黄芩是深有体会的。前人仅笼统地说柴胡、黄芩退热,殊不知“柴胡之退热,乃苦以发之,散火之标也;黄芩之退热,乃寒能胜热,折火之本也”。“予年二十时,因感冒咳嗽既久,且犯戒,遂病骨蒸发热,肤如火燎,每日吐痰碗许,暑月烦渴,寝食几废,六脉浮洪。遍服柴胡、麦门冬、荆沥诸药,月余益剧,皆以为必死矣。先君偶思李东垣治肺热如火燎,烦躁引饮而昼盛者,气分热也,宜一味黄芩汤,以泻肺经气分之火。遂按方用片芩一两,水二盅,煎一盅,顿服。次日身热尽退,而痰嗽皆愈。药中肯綮,如鼓应桴,医中之妙,有如此哉”!
其求实精神,更是可贵。如《范汪方》治健忘方(七月七日收麻勃一升,人参二两,为末,蒸令气遍,每临卧服一刀圭)云服之“能尽知四方之事”。李氏谓其言过其实,“此乃治健忘,服之能记四方事也”。又如古方称“大豆解百药毒,予每试之,大不然;又加甘草,其验乃奇。如此之事,不可不知”。以上所述,都是有人有事,亲历其境,实践经验,很可宝贵。
三、 说理透彻
“发明”中论证的问题,都很透彻,条分缕析,密切联系临床实际,真正能够做到学以致用。如滑石淡渗利小便,这是一般了解的,但不全面,李氏指出。“滑石利窍,不独小便也。上能利毛腠之窍,下能利精溺之窍。盖甘淡之味,先入于胃,渗走经络,游溢津气,上输于肺,下通膀胱。肺主皮毛,为水之上源,膀胱司津液,气化则能出。故滑石上能发表,下利水道,为荡热燥湿之剂。发表是荡上中之热,利水道是荡中下之热;发表是燥上中之湿,利水道是燥中下之湿。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,湿去则阑门通而阴阳利。刘河间之用益元散通治表里上下诸病,盖是此意”。
射干之用,李氏突出降火二字。如云:“射干能降火,故古方治喉痹咽痛为要药。孙真人《千金方》治喉痹有乌翣膏;张仲景《金匮玉函方》治咳而上气,喉中作水鸡声,有射干麻黄汤;又治疟母鳖甲煎丸,亦用乌扇烧过,皆取其降厥阴相火也。火降则血散肿消,而痰结自解,症瘕自除矣。”这样,射干之用,就能得其要领了。
半夏之用,李氏亦有独到见解。尝云:“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,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。涎滑能润,辛温能散亦能润,故行湿而通大便,利窍而泄小便。所谓辛走气,能化液,辛以润之是矣。洁古张氏云: 半夏、南星治其痰,而咳嗽自愈。丹溪朱氏云: 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。聊摄成氏云: 半夏辛而散,行水气而润肾燥。又《和剂局方》用半硫丸治老人虚秘。皆取其滑润也。世俗以南星、半夏为性燥,误矣。湿去则土燥,痰涎不生,非二物之性燥也。古方治咽痛喉痹,吐血下血,多用二物,非禁剂也。二物亦能散血,故破伤打扑皆主之。惟阴虚劳损,则非湿热之邪,而用利窍行湿之药,是乃重竭其津液,医之罪也,岂药之咎哉?”如此文章,能够纠正许多误解。
香附是一味热门药,李氏很为赞赏。其气平而不寒,香而能窜。其味多辛能散,微苦能降,微甘能和。乃肝与三焦气分主药,而兼通十二经气分。如加工炮制,则其用更神。“生则上行胸膈,外达皮肤;熟则下走肝肾,外彻腰足。炒黑则止血,得童便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,盐水浸炒则入血分而润燥,青盐炒则补肾气,酒浸炒则行经络,醋浸炒则消积聚,姜汁炒则化痰饮”。善为配伍,更能发挥它的效用。如“得参、术则补气,得归、芍则补血,得木香则疏滞和中,得檀香则理气醒脾,得沉香则升降诸气,得芎、苍术则总解诸郁,得栀子、黄连则能降火热,得茯神则交济心肾,得茴香、破故纸则引气归元,得厚朴、半夏则决壅消胀,得紫苏、葱白则解散邪气,得三棱、莪术则消磨积块,得艾叶则治血气、暖子宫。乃气病之总司,女科之主帅也”。这里,除了香附本身的功用外,炮制、配伍,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大问题。这在前人是个成功之处,大大提高了临床疗效;而在今天,几被忽视,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果。
又如牡丹皮,治手、足少阴、厥阴四经血分伏火。伏火即阴火,阴火即相火也。“古方惟以此治相火,故仲景肾气丸用之。后人乃专以黄柏治相火,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。此乃千载秘奥,人所不知,今为拈出”。漏芦亦有这种情况,能“下乳汁,消热毒,排脓止血,生肌杀虫。故东垣以为手、足阳明药。而古方治痈疽发背,以漏芦汤为首称也。庞安常《伤寒论》治痈疽及欲解时行痘疹热,用漏芦叶,云无则以山栀子代之。亦取其寒能解热,盖不知其能入阳明之故也”。于此可知,李氏格物致知,明彻事理,功力之深,实堪钦佩。以上所举,仅仅是书中的极小部分,尚有大量资料,值得总结研究,继承发扬。所以说“发明”是《纲目》中的精华所在,直至今天,尚有很高的临床价值。
丁光迪论内科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