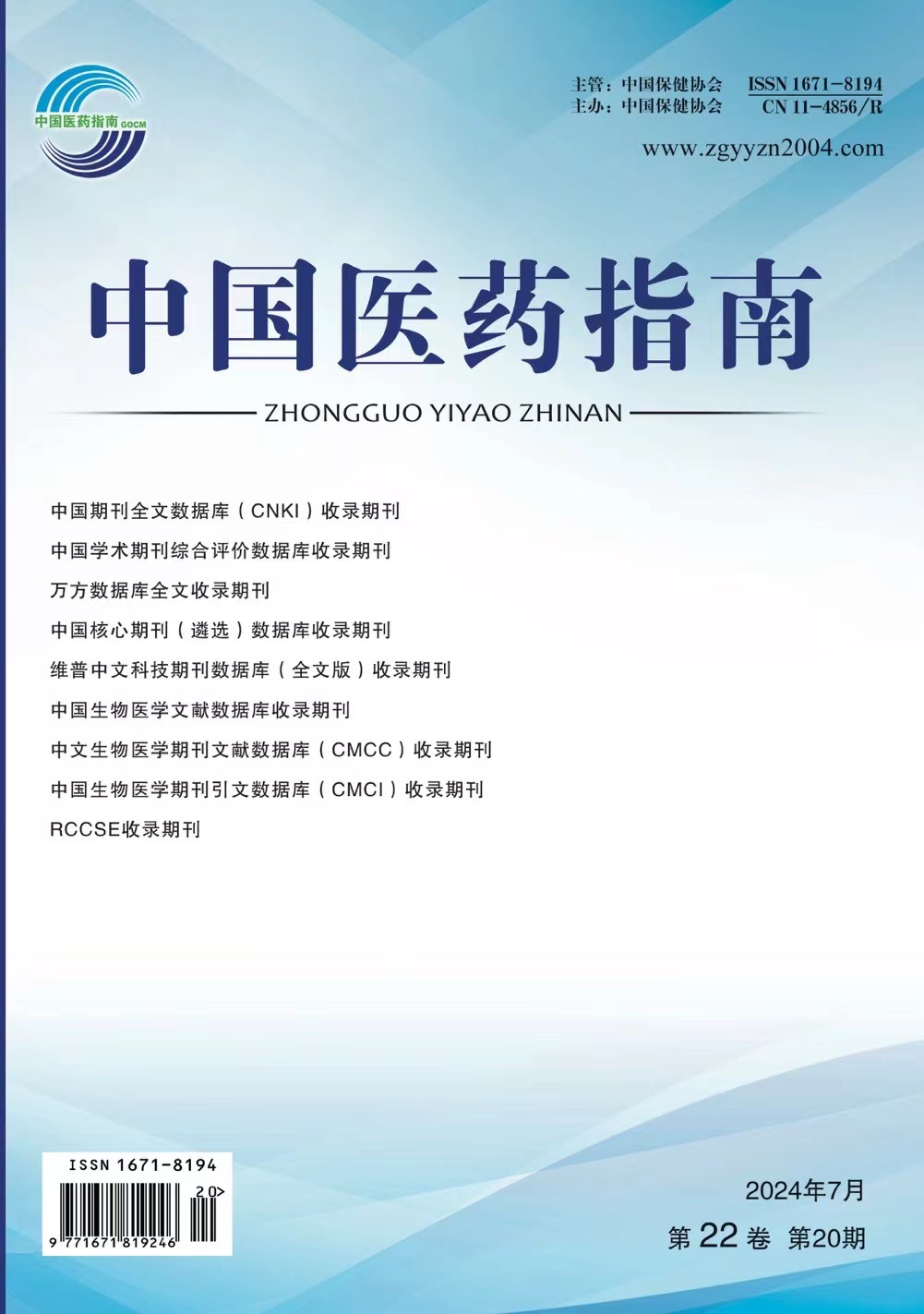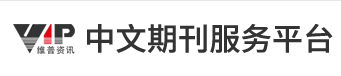伤寒研读
学习《伤寒论》的体会(二)
程门雪
【摘要】
【关键字】
中图分类号:文献标识码:文章编号:
学习《伤寒论》的体会(二)
七
以上所述,主要是谈一些“对于学习《伤寒论》的方法”,现在则看重谈“临床上对《伤寒论》方法的运用”。在运用伤寒方法之前有一个先决问题,就是不可将伤寒的方法孤立起来,在用伤寒方法的同时,必须注意温病学说,用温病学说的同时,要注意到伤寒方法,使两者融会贯通。同时在运用时,要胸有成竹,不可稍存成见。
伤寒、温病之争,虽由来已久,但亦可以毋须争。从两者的病源来讲,六气侵犯,各有不同,故一病一治,各有其宜。所谓“伤寒本寒而标热,温病本热而标寒”,治伤寒刻刻要顾虑其阳气,治温病刻刻要顾虑其阴液。宗伤寒者据“本寒标热”之说,所以在发热时,还主用辛温发散,治温病者据“本热而标寒”之说,所以在恶寒时,就选用辛凉解表。又据清代学者所论,伤寒从肌表而入,所以主张发散。温病从口鼻而入,所以治在上焦,主张清透,即所谓温邪忌表是也。界线似乎分得很清。但在实际临床中,中医治病的“辨证论治”,完全是“因发知受”,在未发以前,无从辨也。已岌之后,有变则变;必须“见微知著”,灵活掌握,不能死据一点,而必须从两方面来看问题。譬如: 初起恶寒微而继即发热汗出、不恶寒、咳嗽、脉浮数的,应用辛凉解表法,从上焦主治,是毫无疑问的;如果初起恶寒发热、汗不出、体痛、呕逆、脉阴阳俱紧的,当然是遵伤寒法、用伤寒方,麻黄汤主之,也是毫无疑问的。如果服一二剂而愈,问题就解决了;亦可以说伤寒、温病是各有其法,断然不同的。如果治而不愈,或得汗后反剧,即所谓“必恶寒、体痛、呕逆、脉阴阳俱紧”如是等等诸症状,则必有其变化了(不变的当然还可用麻黄汤)。能不能变为“颇欲吐,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也”的症状呢?能不能变为“发热而渴,不恶寒者为温病”的症状呢?我们说肯定能。因此,体会到伤寒、温病,不要过分拘泥而绝对划分;温病诸法,大部分都是为伤寒作补充的。一个太阳病伤寒症,既可以转成温病,也有机会转为“反发热,脉沉者,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”或麻黄附子甘草汤的少阴证;只有在临症时灵活掌握,“见微知著”,方能很好地解决问题。
八
伤寒首方即在麻桂,我觉得麻黄汤用麻、桂、甘、杏,和麻杏石甘汤相比较,其中只易一味,此一味之易,即代表了“辛温发散”和“辛凉清解”两个方面。仲景方原是不偏执一点的。伤寒以麻桂治太阳病,而麻黄汤中的麻、杏为肺卫药,桂、甘为心营药,故辨“营、卫、气、血”与温病也并不矛盾的,主要是因寒、因温而取舍有所不同罢了。麻、杏、甘三味是三抝阳,以治风邪犯肺咳嗽,是治在肺卫的方法;增一味桂枝温营,则营卫并顾而为辛温发汗方法,而为太阳病之主方。换一石膏清气,则为辛凉清解法,完全治在肺卫气分。以此推断,即桂枝一味,实为“太阳病,脉浮、头项强痛而恶寒”的主药;如见这些症状,必须用此一味无疑矣;若不出汗的则加麻黄,即成麻黄汤法;若出汗的则加芍药,即成桂枝汤法;有烦躁的则加石膏,即成大青龙法;这些加减、灵活变化,应从“辨证论治”上来考虑,不应当从“风伤卫、寒伤营、风寒两伤营卫”上来考虑。我是反对“三网”之说的。因为“寒伤营”的不能跳过“卫分”,“寒伤营”的还是要用卫分药,麻、杏不明明是卫分药吗?而且今天是“寒伤营”的,可能明天就见烦躁,一变而为“风寒两伤营卫”,所以这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。
再说一说“表虚、表实”问题。一般均讲: 表实麻黄、表虚桂枝;但是用桂枝汤单言治表虚,是非常不妥当的。如果单单表虚,那么应用玉屏风之类以固表止汗,方为妥帖了。应当说: 表实邪盛,用麻黄汤温营开卫;表虚邪留,应用桂枝汤和营解肌;不可忘掉一个“邪”字,这样方是全面。严格来说,桂枝汤的适应证,不仅表虚,而且要里无伏邪者,才可放手用之。如有伏邪征兆者,便当谨慎使用,因为桂枝汤配合桂、芍、甘。姜、枣同用,不独解肌达表,而且能温和其里,所以对“脉数急烦躁为传”之症,桂枝汤较麻黄汤为尤忌,何以故?盖麻黄汤但辛温解表,其妨碍里热之弊犹不显甚甚;桂枝汤则不然矣,倘有伏邪者,服之则流弊百出;所以《伤寒论》特别指出“脉浮缓”,是有其意义的。缓必不数,纵数亦必不甚,或者是虚数,所以桂枝汤症有的十日半月依然不变。伤寒脉紧,即变化最多,此大不相同的。
九
我认为温病用桂枝汤是不对的。吴鞠通《温病条辨·上焦篇》第四条,首列桂枝汤一方,是值得研究的。他说:“太阴风温、温热、温疫、冬温,初起恶风寒者,桂枝汤主之。”这里有许多论点,都可研究。第一,桂枝汤不是治太阴的方子,这在前面我已谈过了。第二,《伤寒论》原文并没有说:“太阳病,但恶热,不恶寒而渴者,名曰温病,桂枝汤主之。”《伤寒论·第六条》原文但说:“太阳病,发热而渴,不恶寒者,为温病。”这是吴氏的杜撰,因“发热”与“但恶热”不同,“发热、不恶寒而渴”者,已不可用;“但恶热”则更甚矣,更不可用了。第三,吴氏又以“温病忌汗,最喜解肌”之说,因而牵合到“桂枝本为解肌”上去,这是误解,且与他后面自己的按语“桂枝辛温,以之治温,是以火济火也”之文自相矛盾。第四,吴氏又说:“虽曰温病,既恶风寒,明是温自内发,风寒从外搏,成内热外寒之证。”既是内热外寒,温自内发,风寒从外搏,如何可用桂枝汤温里解肌!我对吴氏所谓“温自内发,寒从外搏,成内热外寒之证”的论点,完全表示同意,这与我的主张是完全相同的。但对这一个症候仍主张用桂枝汤,则极端反对,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且是有害的,关系甚大,所以必须提出来谈一谈。
十
外感热病,单纯的比较好治,复杂的比较难治。故对单纯外寒用辛温解表、单纯温邪用辛凉解表论治,不作讨论,而对吴氏所谓“温自内发,风寒从外搏,内热外寒”的说法,我最感兴趣。因此,我对大青龙汤之重视,远远超过麻黄汤之上。大青龙汤合麻黄、桂枝、石膏于一方而佐以姜、枣,使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汗,一面仍用麻、桂,不致因石膏之寒而碍表,为外寒束其内热之证出一主要方法(大青龙主证为: 脉浮紧、发热恶寒、身疼痛、不汗出、烦躁)。烦躁乃用石膏之唯一主征。但不汗出而烦躁者,仍当以取汗为第一义。其合辛甘发散、辛凉清解于一方,比较复杂而细致,实开后学无数法门,如后来的九味羌活汤(羌活、防风、苍术、细辛、川芎、白芷、生地、黄芩、甘草加姜、枣、葱)和大羌活汤(羌活、独活、防风、防己、细辛、苍术、白术、黄芩、黄连、知母、生地、川芎、甘草加姜、枣)等,大都由此发源而来,盖法同而药变耳。由于南方人腠理疏松,容易出汗,温病较多,实际上表而不出汗的很少;如果有,必有其他因素,当参合症情,采取其他方法,如助阳作汗、育阴发汗、养营作汗之类等,这就不是纯表所能解决了。
十一
对“外寒内热”与“外邪内寒”的治法,二者是不相同的。譬如《伤寒论》中的“下利清谷,身疼痛”之证,可以先以四逆汤温里,后以桂枝汤解表。因为温里寒之药亦可袪表寒,至少不碍外寒,急其所急,所以先治其里,后攻其表。“外寒内热”之证即不同,若先治内热,必碍其表;先散表寒,必增其热,所以后贤制方,每每表里同治,如刘河间防风通圣双解之类。推其原始,都是从《伤寒论》中的大青龙汤、大柴胡汤、桂枝加大黄汤诸方化裁而来。所以说《伤寒论》为医方之祖,确非虚话。
十二
在透表退热方面,临床中体会到: 柴胡、葛根力量比较大,豆豉、山栀也比较大,桑菊饮则差得多了。某些温病学派,采取山栀、豆豉,对柴胡、葛根则有顾忌,因昔贤有柴胡劫肝阴、葛根伤胃液之说,其实不能如此胶柱鼓瑟来看问题。如果非用不可之时,仍应使用。柴胡可以配养肝阴药同用,葛根也可以配养胃阴药同用,张景岳的归葛、归柴,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如果遇见肌热烙手、不汗出属于“体若燔炭、汗出而散”的病例,葛根和石膏同用,有很大的作用;如果遇见寒热起伏、口苦、脉弦的病例,柴胡和黄芩同用,也起很大的作用。前人有:“早用柴、葛,容易引邪入少阳阳明”之说,完全是错误的看法。我们如能体会到“病由蕴发”的道理,即知苟无蕴伏,决不致剧。同时用葛根以解经邪,即用石膏以清里热;用柴胡以解经邪,即用黄芩以彻里热,这正是顾到表里两面的办法。所以对昔贤之并用羌活、葛根、柴胡、石膏、黄芩于一方之法,未可厚非。如陶节庵之柴葛解肌汤便是。这种方法,原则上我是赞同的。如果有汗而苔黄、舌尖红,便可了解到这种热不是一汗能解,则当慎用了。如果已见伤阴现象,当然更值得考虑。
十三
在清热退热方面,伤寒用石膏、黄芩、黄连,温病也用石膏、黄芩、黄连,此点并无不同,但温病学家发展了一个“轻清气热”法,如银花、连翘之类;发展了一个“凉营泄热”法,如犀角、生地、丹皮、茅根之类;发展了一个“芳香开窍”法,如至宝、紫雪、牛黄丸之类;这是很突出的,在辨证论治上,各有其适当的地位,可以补充《伤寒论》方法之不足。
十四
在“下法”方面,伤寒与温病,都有应用的时候,至于轻重、早晚之不同,也不过举其大概而已,分别也不大。唯有对“谵语”一症,《伤寒论》除热入血室外,大都用下法,只有一条是用白虎汤的。临床中遇到潮热谵语而一下可愈的,似乎不很多见。相反,凡热病而见谵语妄言者,每属重症险症,且多与热神昏同时并见。温病学家补充了“清心开窍、泄化痰热”,如紫雪、至室、神犀一类方药,是非常可贵的,因为这是重症,有性命危险,添一个好方法,即添一分大力量,如何可以不加重视呢?我的体会是: 伤寒之潮热谵语,单纯属于燥屎症者,是不十分重的,如果壮热、神昏、谵语同见,单单一下,很难解决问题,必须配合温病学说,分别在气、在血,进行处理。如果壮热、神昏,不大便而苔老黄于糙的,此属热效熏蒸心包,症属有热亦有结,应用白虎合承气法;如果大便通的,白虎加人参汤殊为有效。在《伤寒论》中有:“三阳合病,腹满身重,难以转侧,口不仁,面垢,语,遗尿。发汗则语,下之则额上生汗,手足逆冷,若自汗出者,白虎汤主之。”此即唯一说明谵语不可用下之条文,这是关键性文字,极要注意。临床中体会到象这条的症状,应当用白虎加人参汤,比单用白虎汤更为有效。如果壮热神昏、谵语妄言,苔黄腻而不干燥,大便通的,此属痰热蒙蔽心包,应当泄化痰热而开窍闭;如果舌苔红绛的,即属热邪入营、内陷心包,用气分药是没有效的,就非凉营清心不可了。伤寒用下,仅限于潮热、谵语一证,并非全部包括高热神昏在内。“潮热”与“壮热”,距离很大,不能混为一谈也。
十五
讲到心下痞满,伤寒、温病同有是症,唯《伤寒论》强调由误下而成,所谓“病在阳,下之成结胸;病在阴,下之因作痞”是也。但临床所见,不由误下亦见胸痞之象。盖湿热郁结于中,可以致痞;热结于中,亦可致痞;中阳失其转旋,也可能见痞窒之假象。《伤寒论》三泻心之治痞,大多数是无寒热、或虽有而甚微,同时又属屡经误下而见下利清谷、腹中雷鸣、下虚上实、下寒上热之象,所以可用苦辛通降治上,扶正温中治下,二者合为一方而施治。反过来,如外症未除而数下之,心下痞硬,协热而利,利下不止之症,又当温中解表而用桂枝人参汤为治矣。三泻心证之下利。腹中雷鸣,是误下所致;而胸痞是湿热痞结在上,未必因误治始然;桂枝人参汤症之协热而利、利下不止,是误下所致,其心下痞硬,乃中阳不运、阳气失其转旋使然,也由误下所致,故可用理中汤温运中阳,桂枝通阳开表为治;但必须注意舌苔,其苔定是白薄的;如果黄腻的,就非用泻心不可了。
热结的痞,也分两法: 一是用栀豉宣通,一是用大黄黄连泻热,其分辨主要也在舌苔,苔薄黄浮滑而心中懊的,主以栀豉;苔黄沉着而口苦燥,大便不行的,主以大黄黄连泻心汤。栀豉有表热,泻心无表热,亦是一据。温病中胸痞最多,尤其在湿温症中更为多见,这两个方子,都有应用之处。湿温胸闷,对泻心之辛开苦泻,尤为相宜,但不可漫用原方,因湿温之胸痞,不是误下而成,没有下利、腹中雷鸣诸症,方中干姜一味,用时尤需谨慎,一般都以厚朴代之。至于轻苦微辛法,用杏仁、蔲仁、橘皮、桔梗之轻灵流动,更可补前人之未备。总之,治心下痞结、胸痞之法,栀豉与大黄黄连是一对子,一用清而宣,从表解;一用清而泄,从里解。三泻心与桂枝人参汤又是一对子,同样下不利、心下痞硬,一则虚实夹杂,温清同用;一则里虚有邪,温运通阳。用《伤寒论》方,必于此等必再三致意,方为有得耳。
十六
在“三阴”方面,温病学者强调“救阴”,认为要处处顾其阴液;伤寒学者则强调“回阳”,认为当处处顾其阳气。这是两派不同之处。但是“伤阴”与“伤阳”,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,只有多少之分耳。《伤寒论》少阴篇中既出“但欲寐”之亡阳证,用四逆法;又出一“心烦不得卧”之伤阴证,用黄连阿胶汤(为温病定风珠方之祖)。温病学说亦注意病人的面色,若色白者,就要顾其阳气,所以温病学说既发展了“救阴”方面的方法(甘寒养胃、咸寒育肾等),同时也并不排除“回阳”的一面,不过稍有区别,即所谓“阳不回者死,阳回而阴竭者亦死”。因为温病的亡阳,是由伤阴之基础上来的,其病日比较长,不似伤寒之亡阳来得陡暴,故在回阳之中,必须顾其阴液,如用到附子,必须兼用阿胶、生地,或兼用龙骨、牡蛎、白芍等。倘使单用四逆以回阳,就容易导致“阳回阴竭”,这就是“阴阳互根”的原理。根据《伤寒论》规律,四逆汤主回阳,白通汤主通阳;临床所见,四肢逆冷之症,多出现于病之后期,多数为正气不足、虚阳欲脱的情况,故用四逆成方的较少,而以用参附龙牡的居多。至于白通与四逆的区别,前者用葱白,后者用甘草;用甘草是回阳,用葱白是通阳,两者作用不同。但用到“回阳救逆法”时,每属病之末期,应以参附龙牡为佳;用“通阳破阴”法时,其病不一定在后期,而属严重症状之一。
《伤寒论》出白通汤之条文中,只有“少阴病,下利”五字,似乎不够明确,然根据《伤寒论》 315条白通加猪胆汁汤和 317条通脉四逆汤的加减法来研究的话,似乎需要通阳的有二症: 一是厥逆无脉,这可算是阳气不通;二是面色赤,也可算是阳气不通;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症状,即是小便不通。叶天士治臌胀,对大腹膨胀、阴浊凝聚而小便不通的,每用白通加猪胆汁汤,所谓“通阳不在温,而在利小便”,即其意也。总之,用四逆汤治大汗、大下利而四肢厥冷的症状是容易处理的;治下利、四逆而兼烦躁、面赤、咽痛、反不恶寒等症状——所谓“真寒假热”现象,便是更进一步的治法,其脉不一定微细,可能是豁大而空;舌苔不一定白润,可能是灰黑而唇焦,但看去虽焦黑,指按之原是润泽的。阴证而面红舌黑者,是常见的,总以脉大而空为准。如果下利不甚者,景岳六味回阳饮最为有效。还有人字纹舌苔,其舌苔白滑而作两歧,宛如刀割,昔贤有“阴证误服凉药,舌见人字纹”之语;更有舌色如珠,症见畏寒发热,下体如冰,虽饮沸汤亦不知热者,此为肾水凌心,逼其心阳外露,亦可用六味回阳饮治之。
十七
《伤寒论》357条的麻黄升麻汤症,即是四逆汤症的一个很好对照例子。麻黄升麻汤的见症是: 泄利不止,手足厥冷,脉沉而退,完全符合四逆阳的主症,但是有一特异点,即咽喉不利、吐脓血、不汗出是也。“咽喉不利”一症,与通脉四逆条之“或咽痛”犹难区别;但本条所述,不仅“咽喉不利”,且有“吐脓血”;不但吐脓血,而且不汗出,明明是未经发汗而妄用下法,以致上热闭郁,兼虚其中发生这些上热下寒之症。因此,必须另出一个方法,即: 合发表、清上、温中三法于一方,是为麻黄升麻汤的方旨。此方着重在取汗,故方后云:“煮取三升,去滓,分温三服……令尽,汗出愈。”以前诸家,认为本条不足取,其实是没有细玩原文(尤其是方后语,如玉苓散之多服暖水,汗出愈。亦然)及时对比所致。我从前也是如此,后来渐有体会,深知复方有复方的好处,复杂的病必须用复方来治。《伤寒论》中如本方及乌梅丸、柴胡龙牡等方,均是复方,但此条所述,则更为突出耳。
十八
讲到厥阴病,《伤寒论》的原文确是太简单了,论中所载的许多“厥”,都是作比较的,原文必有散失,当无疑议。厥阴篇中所述,以热与厥反复发作为主征;厥阴之厥与少阴之厥显然不同,它是以寒热夹杂之症为多,所谓“厥深者热亦深,厥微者热亦微”,治之不善,每易见“口伤烂赤、便血”等热症。然而这些内容,只不过是引头而已。对于厥阴病之重症如: 舌卷、囊缩等,篇中没有提到;痉厥动风等,也没有提到;主客交混、气滞血淤、神昏形默等症,也没有提到。温病学者在这几方面作了很大的补充,有了很大的发展。例如: 大小定风、三甲复脉法之对痉厥动风,加减三甲散之对主客交混,鲜首乌、鲜生地、鲜芦根、稻根之对硬囊缩、神昏发痉等,都是非常精到的办法;至于大便坚加大黄,则为厥阴阳明两治之妙法,盖症属厥阴阳明同病也。亦即泄热存阴之义。少阴病篇中的三条用大承气急下存阴,亦正是如此道理。此三条既非完全少阴病。亦非故意列入少阴篇中以与少阴病作鉴别,而是少阴与阳明同病也。
十九
在少阴篇中的四逆散(甘草、枳实、柴胡、芍药),根据方剂的药性,完全不是治少阴病的,应当列入厥阴篇内。因为方药的功能,乃是从经验的累积而得到的规律,不能随人意志而漫为转移的。《伤寒论·少阴篇》这条原文,其主治只有“四逆”二字,其他都是或有证(或咳,加干姜、五味子;或悸,加桂枝;或小便不利,加茯苓;或腹中痛,加附子;或泄利下重,加薤白等。),是不够明确的。我的看法是: 其所主治的“四逆”,既非亡阳,也不是热深厥深。如果是亡阳,应该用四逆汤;如果是热深厥深,应用犀、羚或白虎汤。其所主治之症,应着重放在邪郁结给不舒上面(此症为临床所常见,故本方应用机会亦多),虽见手足冷、脉沉细紧,不得谓之阴证。辨证的第一要点,应当是大便硬或是泄下而下重;第二个要点是: 身无汗,或但头汗出;所谓阳气一郁,不但阳症似阴,阳脉亦似阴也。总的说来,从临床体会来看,《伤寒论》的方子,用之得当,疗效很快;若用之不当,其流弊亦很多(不是指《伤寒论》中的所有方子而言)。所以必须看得准,用得确当。如果学“温病派”的人,只会用温病方子,不会用《伤寒论》方子,那就太局限了,成绩不会太大的。反之,学“伤寒派”的人,如果只守《伤寒论》之方法,拒不接受“温病学派”的种种发展,其弊亦然。
二十
外感热病,都有从阴从阳两个方面,都有从虚从实两个方面。关于从阴从阳方面,上面已谈过了,兹不复赘。
从虚从实问题,即“邪”与“正”之间的关系。在具体处理过程中,是祛邪以存正呢、还是扶正以达邪?譬如伤寒温散,首重麻桂,景岳用温散,即以理阴煎加麻黄,或麻桂饮、大温中饮为增减。对劳倦内虚感邪而不得汗解的人,用之有效。虽一从阳分、一从阴分,其路若异。然而一则为逐于外、一则为托于内,而用温则一。治温病之用黑膏、复脉,亦同其例。
人是一个整体,脏腑经络,不能孤立起来看,其间都有联系;不过以何者为重点,即有不同。讲《伤寒》必须研究《温病》,学《温病》必须在《伤寒》的基础上来进行,既要承认《伤寒论》的重要指导意义,又要承认后来诸家对“温病学说”的发展,认真做到如此,才能胸有成竹而无成见。
程门雪论外感病近代名老中医经验集